|
视频|专访小提琴家王之炅   王之炅专辑 斯特拉文斯基&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 Q1.从你这次音乐会的一首曲子开始话题吧,勃拉姆斯《谐谑曲》。这首曲子的动机,源自小提琴大师约阿希姆的座右铭“自由而孤独“。
王之炅:首先,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说,孤独是必然的。我们这个职业最大的特点是,比一般人在某些点的感触更多,感触更多,渴望表达和探索的就更多。 其实,我不是那种很悲观,很多愁善感的人,我性格还是比较乐观的,但仍免不了一些敏感性。在寻找自己内心的渴求时,要做很多努力,去跟内心妥协。 这是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你的,也没有办法跟人讲述的。我觉得自由源于孤独,越自由,越孤独。 Q2. 你认为,艺术家是否注定孤独? 王之炅:我是一个完全可以沉浸在孤独里的人,对我来说,孤独完全没有问题。在追寻内心渴求之时,一定是孤独的,因为你想要的东西,别人爱莫能助,你也难以与人倾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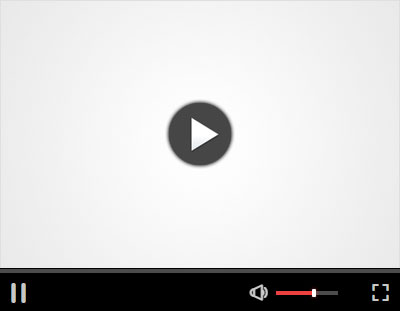 蕾拉·奥尔巴赫《孤独组曲》 Q3.你提到过,你常去聆听跟你风格很不一样的演奏,从中汲取灵感,拓宽思路。我很好奇艺术家之间,这种微妙的影响具体是如何产生,如何取舍的? 王之炅:一个艺术家越走到深处,就越会去深究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很多时候,越往一个方向探索,道路会变得越狭窄,甚至会变得过于偏执。此时,需要去修正自己。 为什么很多人会评价一些演奏家,觉得他们在三十多岁时艺术水准最佳,然后到了他们四十岁、五十岁时,我个人感觉他们的演奏是更机智、更自我了,但很多人不就喜欢了,因为他们走向了偏执的道路。 其实,在偏执的路上,还是要不断去修正自己,修正自己的方法就是拓宽自己的视野,不要一门心思钻到自己的牛角里去。 我需要往自己内心深处的方向走,也需要主动去接纳一些东西来修正自己。固执有时候是好的东西,有时候是不好的东西,我知道一些固执是不好的,所以主观上,希望有什么外来影响,能让我主动修正自己。  王之炅在德国的老师Kolja Blacher 他曾是柏林爱乐和琉森节日管弦乐团首席 Q4.你在国外最重要的一位老师是Kolja Blacher,我们都知道他是阿巴多最信赖的搭档,也身兼独奏、首席、室内乐、指挥等多领域,才华横溢却十分低调,谈谈他对你的影响吧。 王之炅:首先是职业精神,他的职业精神,绝对是我见过的音乐家里首屈一指的。在我们排练一部重奏作品,或学习一首协奏曲时,他会告诉你,所有的责任都肩负在你身上,不应该指望任何人帮你掩饰,没有做好功课就不该参与排练。这是我从他身上,学到至关重要的一点。 其次,他拓宽了我的视野,我在去德国之前已经拉过一些当代作品,比如斯特拉文斯基、普罗科菲耶夫的协奏曲,这些在德国人看来算不上很前卫了,他有帮我将继续拓展到一些非常前卫的作品了。后来,我之所以敢于去首演一些作曲家的音乐,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给了我知识和启发。 Q5.你曾说过,他的风格不见得适合别人,但非常适合你,能否具体谈谈这一点? 王之炅:我所说的他对别人不一定合适,是指教学方面,不是音乐方面。在音乐方面,他是一位公认的高级而不炫技的音乐家。我觉得他这样的音乐家是跨乐器的,不管去演奏什么乐器都可以是高级的。 我自己则更倾向于一位器乐演奏家,而他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家型的音乐家。无论作为独奏、重奏、首席还是指挥,这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。 他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海菲茨、奥伊斯特拉赫那种炫技型的演奏家,他是纯粹音乐性的,在德国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音乐家。  王之炅年少时与梅纽因大师同台 Q6.你和一些老派传奇小提琴大师,有过令人羡慕的交流合作经历,比如梅纽因、吉特里斯,他们似乎都很喜欢中国文化,谈谈与他们的交流体验吧。 王之炅:与梅纽因合作时年纪还太小,很多东西无法深入探讨,因为年龄差距差太大了。我印象中他也有教过我一些东西,可能就一两句话,但这一两句话我过了十几年才会懂。 说起老派的演奏家,我其实跟吉特里斯的交汇更多一些,他是在我年纪稍长后与我有一些交流。 他跟梅纽因一样,很喜欢老子,我觉得很有意思,为什么国外的音乐家这么喜欢老子。我们之间讨论的不仅有老子,还有一些音乐方面的问题。 Q7.吉特里斯的确是一位很有意思的大师。你觉得大师云集的“黄金时代”,与当今神童辈出的互联网时代,有哪些方面的时代差异? 王之炅:就音乐方面而言,吉特里斯这个年代的音乐家,比我们自由的多,我很羡慕嫉妒,因为他不需要关注任何的市场问题,他只需要关注他自己,他只需要做好他自己。
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勇气,他一直对我说:你必须要有勇气。还有一点就是,到底是注重故事的规则更重要,还是把故事说出自己的道理更重要?这给了我很多启发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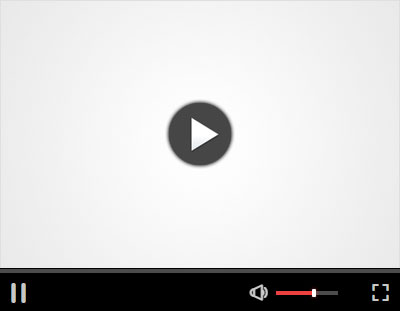 恩斯特《夏日最后的玫瑰》 Q8.你提到过,你喜欢逻辑严谨、结构精妙的音乐 比如巴赫、巴托克、贝尔格的作品,你称之为“高度智慧的音乐” 。 你崇尚自由,却也痴迷结构,这让我想到斯特拉文斯基的一句话 “艺术越是受到限制,越是经过推敲,越是自由的” ,你怎么理解这种对立统一? 王之炅:你对一个东西的规则越熟悉,你越知道怎么去玩好它,我觉得这一点都不矛盾的。
Q9.那么,在你看来与“高度智慧的音乐”相对应的,是什么类型的音乐? 王之炅:纯粹情感冲动的音乐,比方说,拉赫玛尼诺夫。我不是说他的作品没有结构感,但相对来说感性更多。结构和情感,这两样东西对作曲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,但不同的作曲家会有不同的偏向。 Q10.这次在上海的音乐会,你会演多首舒曼的作品,舒曼在许多音乐家看来很“神经质” ,你会把他的音乐该归为哪类? 王之炅:这个要看阶段,我将要演的舒曼《第一小提琴奏鸣曲》还是相对比较有结构感的作品。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,对于作曲家来说,无论如何都会有结构和情感这两方面。说到舒曼有神经质的一面,的确是,他很多时候不按常理出牌。 另一方面,哪怕是勃拉姆斯这样一位所谓的理性大师,他都会说自己的音乐是阴差阳错而来的。所以我们很难用一个词,理性或神经质去定义一位大师,他们有太多方面了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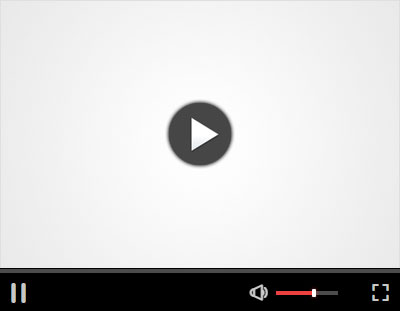 古拜杜丽娜《奉献》 Q11.除了大量古典派和浪漫派曲目外,你也十分热衷演奏现当代作品。对于普通听众来说,现当代音乐“很不好听” ,你觉得,演奏家该怎样让听众更好接纳这类作品? 王之炅:我觉得这个很难,对于普通听众来说,很需要的是抓住一个很好听的旋律或和声,否则很难抓住一首作品的欣赏点。 但这并不要紧,因为音响与和声在变。听众的耳朵熟悉了一个时代的音响与和声,慢慢也会走进另一个时代的音响与和声。 可能是在二十年后,大家会习惯并意识到这是好听的,这需要时间,音乐家总是领先那么一些的。不用担心,也不需要解释,好的东西自然会留下来的。 Q12.现当代作品吸引你的点在于? 王之炅:我是一个很喜欢新鲜事物的人,我喜欢去学习一些有意思的东西,现当代作品对我来说就很有趣味,我想要去理解、去演奏、去学习这种我原本不理解的语言。
那么,我看到了新鲜的东西,就会很好奇。对我来说就像学习一种的语言,进而发现这种语言很有意思,所以就会分出一部分精力去学习演奏现当代作品。 塔尔蒂尼《魔鬼的颤音》 Q13.如今,很多人都能掌握高超技巧 但真正“大师级”的演奏却不常见 有一些老派小提琴大师指出 在当下“深层技巧”普遍缺失 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? 王之炅:技巧分两个方面,一种是炫技的技巧,还有一种是更为深层次的,可以用来表现音乐、可以表现各种音色、可以将音乐深层次内涵表达出来的技巧。这种技巧的缺失,会让音乐听起来很苍白。
音乐家想要上升到一定层次,需要两个方面,一方面是要有演奏和表达等多方面的能力,还有一方面是审美,审美是至关重要的。当你有能力时,才能够去输出自己的审美理念,但我认为,很多时候问题就出在了审美理念上。 年轻的演奏家想要在舞台上有一席之地,需要有听众的支持,需要来自经纪公司或指挥等多方面的支持,所以会考虑如何让大家喜欢。但是,我有一句听起来很傲慢的真心话:如果我们音乐家,审美和大众保持在同一水平,那要我们做什么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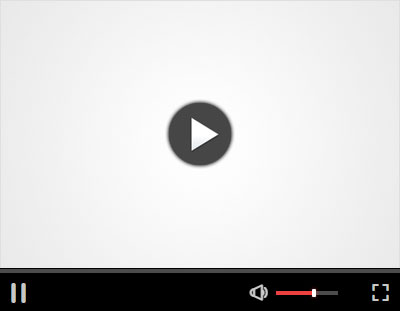 王之炅演奏《梁祝》 Q14.刚才,我们谈到了演奏者的勇气。老一辈的小提琴家里,与你合作过的克莱默、吉特里斯都是公认的怪才,近几年大红大紫的Kopatchinskaja更是离经叛道,那么,演奏家的“大胆”该有尺度吗? 王之炅:我觉得这几个人要分开来说,其实科Kopatchinskaja和克莱默等人是截然不同的。
演奏家有很大的自由度,但是要建立在一些规范之上,否则就会出格。但是,这种出格的演奏,市场不见得不喜欢,甚至会很喜欢,因为她有新鲜感。 我也会去听Kopatchinskaja的音乐,我会去从中找到一些能启发我的亮点,这个亮点不一定是她的优点,但我看来是她的亮点。我不会抗拒去听她的诠释,但我不认为这样的音乐家会成为主流。  沈叶《缄默诗篇》 Q15.最后,我们谈谈中国小提琴作品。中国作品也是你常演的,有些很传统,有些很前卫。除了《梁祝》为代表的几首大众曲目外,有什么你个人比较推崇的作品吗? 王之炅:中国小提琴作品确实不多,现在还在被大量演奏的就更少了,新写出来的一些音乐有的非常好,但没那么旋律化,缺失了一些普通听众喜欢的元素,所以现阶段无法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作。 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部是沈叶写给我的小提琴协奏曲《缄默诗篇》,这是我这两年演奏过的新作品里特别欣赏的一部,它有很深层次的音乐内涵,有我喜欢的音乐语言和很强的逻辑结构感。        专辑欣赏:《梁祝》与《缄默诗篇》
    |
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