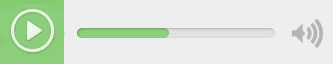如果有来生,我想做一株草木,或者,某一种低等的动物。
一对狗,在大马路上缠绵纠缠,打都打不散,即使赤裸裸,即使被骂做狗男女,那又怎样,它们毫不在意。
某种程度上,我羡慕它们的这种坦荡。
我也羡慕树,花,草,只要喜欢,就可以在风里招摇,哪怕,招蜂引蝶。没有流言,也无所谓蜚语,更无,所谓道德伦理的约束。
喜欢阮籍。
喜欢他,在母亲的丧礼上可以不流一滴眼泪,痛,灼在心里,泪,亦流往心底,绝不,对!绝不表演给人看!
喜欢邻家已婚的少妇,那就直直白白的说,我喜欢你。想和她坐在一起聊天,那就青天白日地聊;累了,索性趴在她旁边酣然入眠。
嫂子回娘家,他牵头小毛驴,大摇大摆地护送。一程又一程,依恋,就是依恋。
管他大眼睛,小眼睛,还有什么管中窥睛。
他所谓的猖狂,不过是至真至纯,不过是,一清如水,不过是一颗素心坦荡天地间。
也喜欢齐白石。八十几岁的高龄,第一次看见新凤霞,就痴痴地看,直愣愣地盯着看,旁若无人地看。看得众人尴尬了,他,还是看。
“她长得这么好看,我喜欢看。我要大大方方地看!”
多坦荡,多可爱。
新凤霞,不愧是新凤霞,酒窝绽开,嫣然释笑,齐老,您好好看吧,我是唱戏的,不怕人看的。
喜欢上吴祖光之后,她直接就说:“我喜欢上你了,怎么办?”那时她只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戏子,而吴祖光是有名才子,比她大十多岁,又离过婚。面对流言蜚语,她说,“快点,我们结婚吧。”
后来,新凤霞师从齐白石学画,成为文坛佳话。跟着吴祖光学认字,学写作,后来居然成了大家,无论是绘画,还是写书,均是上成。
这,绝非偶然。她,认真做自己,没时间在乎蜚短流长。
还有鲁迅和萧红。我讨厌后人的无端揣测,孤单寂寞敏感多情一生凄苦无依的萧红对鲁迅的情感的确复杂,鲁迅于她,是尽心栽培青年才俊的人生导师,是他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忘年老友,似宠她爱她的祖父。就算是情感依恋的对象,又有何不可。人性本就多面,人情本就复杂。只要发乎情止乎礼,坦然面对,又与人何碍?
如果,有一天,我写小说,我一定写一个女性,她可以是小女生,她可以是少妇,他可以是中年妇女,但她一定会,遇见不同的男性,只要她喜欢,她尽可以坦然地说,我喜欢你。我就是喜欢你呀。对方呢,哈哈一笑,惊喜道,“啊,我也喜欢你呀。”然后两人就如青草相依,拥抱,离去。坦荡无迹。就如刚好天空划过一阵风。
我讨厌猜忌,讨厌揣测,讨厌小心翼翼,讨厌被误会。
我知道,路遥知马力,日久见人心。太阳每天升起,人心仍然并非日月可鉴。

但,这也没什么,我就是喜欢你,像风喜欢树,那就刮过去,告诉它。
幸好,我有阿渡。我可以大声、小声地告诉你,你们:”我喜欢你,你们!“